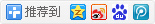你還記得那天與他初遇時的天色,還存著那些夜里他為你唱的歌,還常去那家他帶你吃的深巷面館,還留著那件藏有梵尼蘭味的牛仔外套。在空余的午后,你又泡了一壺茶,茶葉是隨手拿出的一撮。你本想小口斟酌,卻鬼使神差一口牛飲,仿佛他在一旁嫌棄你做作。你控制不住想罵人,卻又強忍下躁動。拿出信箋,你一字一頓的寫下:你留下的行李會被打包帶走,你送我的禮物會被一一退還。這樣的話,你還能銘記我多久?

?每日推薦:布衣生活?,?全世界都在磕我和影后的CP?,?穿成炮灰攻后我禁欲清心?,?情有獨鐘宋晗?,?空間小農女:致富種田忙txt?,?烏魯克的閃恩二三事?,?論與室友相處的必要性?,?超小乳頭綜合癥?,?出軌后我又出軌了(NP)?,?從監獄走出的狂少